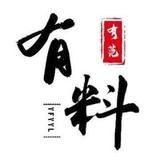“沒有副軍長,沒人敢當。”
1946年,起義軍38軍迎來了一個神秘的副軍長,他的名字無人知曉,來自西北軍,過去沒有任何顯赫的戰(zhàn)績。
帶領(lǐng)部隊走過無數(shù)的艱難困境,他最終打破了常規(guī),將一支瀕臨崩潰的軍隊,帶入了勝利的軌道。

沒有副軍長,不是因為沒人,是沒人敢當
陳賡看著這份名單的時候,皺了眉頭。
“你這是在玩命。”他對毛澤東說。

毛澤東沒回答,他一字一句讀那份電報,不是轉(zhuǎn)發(fā),是手寫。
上面說得很清楚,38軍要過黃河,去豫西,配合中原局,打國民黨十萬精銳,不是佯攻,是主攻。
“沒有副軍長,你讓孔從洲一個人帶著原國民黨兵打仗?”
他翻過檔案,只有一個人選,劉威誠,但是這人有問題。
他是西北軍的老底子,跟張學(xué)良有關(guān)系,常年在西安,黨齡不短,但戰(zhàn)法保守。

劉威誠
操著老軍閥那一套,新兵上來沒幾天就被他“整頓思想”,結(jié)果軍心一片混亂。
38軍在晉冀魯豫訓(xùn)練了半年,一共換了三撥軍政干部,都頂不住壓力。
這不是軍隊,是火藥桶。
毛澤東那天沒說話,只在電報末尾加了一個名字:“陳先瑞,調(diào)任38軍副軍長,分管作戰(zhàn)。”
沒人提過這個人,戰(zhàn)史里也查不出他和38軍有任何交集,但三天后,他就穿著八路軍的舊軍服,出現(xiàn)在新鄉(xiāng)。

他沒帶警衛(wèi),連槍都沒帶,第一句話是:‘你們打的地形,我走過三年。’
孔從洲愣了,他不認識這人,但他記得陜南那邊的仗,就是靠人背槍爬山、藏在石縫里挨餓打出來的。
“你是哪個部的?”
“74師。”
孔從洲臉色變了,這不是哪兒都能隨便喊出來的番號。

這個人,有歷史
1932年,湖北麻城,一個小班正在清點物資,9支步槍,4發(fā)手榴彈,一個班只有6個人。
班長姓陳,不高,眼睛細,他不說話的時候沒人注意他,一說話,沒人敢插嘴。
這支部隊叫鄂東游擊司令部特務(wù)四大隊,他帶的小兵里,有一個后來成了赫赫有名的韓先楚。

韓先楚學(xué)打槍,是他教的。
不是在靶場,是在稻田邊,他們趴在爛泥里,把一只破飯盒掛在樹枝上練瞄準,沒靶紙,只有風(fēng)聲。
1934年,陳先瑞被調(diào)去陜南,沒人愿意去那里,山高、林密、人少,敵人多,補給難。
他帶的隊伍是74師,原本是紅軍里編制外的散兵。
到1940年,他們不再是“編外”,他們成了陜南的主力,打了十幾場小仗,殲敵三萬。

有一年冬天,敵軍圍山,他帶隊突圍,在雪地里趴了兩天,回到根據(jù)地時,手指凍掉兩節(jié)。
他說:“能打就行,寫字的事以后再說。”
1944年,豫西抗日三支隊成立,政委叫陳先瑞,職務(wù)從作戰(zhàn)變成政工。
他只干了一件事——“改造人”。
收編的舊軍隊,照規(guī)矩,政治審查、集中整訓(xùn)、交槍、換編制,他換了順序,先讓他們“打一次仗”。

“打完再整頓。”
“打得贏,留下來;打不贏,沒人追責(zé)。”
結(jié)果第一仗打的是地方頑軍,繳了92支槍,隊伍只跑了11個人。
他做到了黨校沒教過的事情,把舊軍隊的腦子,換成自己的。
毛澤東記住了他,沒有官方褒獎,沒有授勛,只有一條記錄:“此人擅長邊區(qū)游擊,改造能力極強。可用。”

1947年8月,中央軍委一紙命令,把陳先瑞調(diào)去38軍。
不是提拔,是補位,不是升遷,是賭命。
38軍要渡黃河,目標是鞏縣、汝州、魯山。這是國民黨設(shè)防最密的區(qū)域之一,李延年帶著整編第十一師正面布防。還有兩個機動師隨時增援。
他們不信起義部隊能打硬仗,陳先瑞信。
他提出一個要求:先不打正面,打背后,用38軍的17師夜襲敵軍后勤。
孔從洲反對,理由是:17師剛改編,不熟地形,沒經(jīng)驗。

孔從洲
“我?guī)ш牎!?/p>
他沒有再解釋,他熟豫西,是事實,他布防圖都畫得清楚,哪條山路能通車,哪條只能徒步,他用樹枝在沙地上畫出來,一寸不差。
作戰(zhàn)命令發(fā)出三小時,17師悄然繞道黃河西岸,敵軍毫無防備,后勤被炸,糧道斷絕。
正面戰(zhàn)場的38軍順勢推進,一周之內(nèi)收復(fù)三個縣,這是38軍第一次打大仗,第一次勝利。

孔從洲
是一次“舊兵變新軍”的臨界點。
孔從洲后來在報告里寫:“如果沒有副軍長帶17師,我們現(xiàn)在可能還在整訓(xùn)。”
沒有贊揚,沒有溢美,只有事實。

他不是英雄,卻改變了一個戰(zhàn)局
靈陜戰(zhàn)役前,38軍士氣并不高。
原國民黨軍出身的兵,很多還留著舊制帽徽,有些干脆把徽章縫在棉衣里,說是“留個念想”。
新來的干部一遍遍開政治課,講統(tǒng)一思想,沒人聽,夜里還有人打架,罵人“叛徒”。

這是起義軍的命,不是統(tǒng)一軍隊。
陳先瑞不講課,他不訓(xùn)人,他只干一件事,把地圖掛在墻上,畫箭頭,箭頭指著靈寶和陜縣交界處。
敵軍有一個營據(jù)守那兒,是通向陜南的咽喉要道。
“這仗,我們單干。”孔從洲聽完,臉色變了。
“你知道那營是誰帶的?”
“整編第36師殘部,第三營。”
“張志超帶的。”

陳先瑞
張志超是原西北軍出身,跟孔從洲是同門,也是舊人,打過北伐,槍法快人狠,說到底是他們自己人。
“他帶的兵,都是沒投共的老弟兄。”
“你確定要打?”
陳先瑞點頭:“不打,他們永遠不會信你是真的轉(zhuǎn)了身。”
起義軍想真正融入,必須砍掉過去的尾巴。
戰(zhàn)斗打了六個小時,38軍17師強行軍五十公里,夜襲敵陣,陳先瑞帶的先頭連,從山脊下切進去,打掉了敵軍指揮所。

張志超沒跑成,被俘時還穿著舊軍裝,子彈打光了,扔槍罵娘。
“你們真打啊?瘋了吧?”
沒人接話,士兵們冷眼看著他,一步步把他押下山。
第二天,孔從洲親自寫了戰(zhàn)報,不是給上級,是貼在連隊墻上的。
“我們不是舊軍隊。”靈陜戰(zhàn)役后,38軍變了。
開始有人摘掉舊帽徽,開始有兵主動申請調(diào)到戰(zhàn)斗班,沒人說“我是舊軍人”。

陳先瑞沒講一句話,他走進每一個連隊,默默看訓(xùn)練,誰槍法差,自己改靶,誰走位慢,親自帶著爬山。
最小的一次行動,抓的是一個敵軍的探子,他只說一句:“看見了沒?他們還在盯著我們舊底。”
沒有批評,沒有口號,只有仇,38軍從此有了骨頭。

他沒有上將軍銜,但每一仗都壓著上將打
1955年授銜,名單下來的時候,38軍的人都在看一個名字,不是軍長,不是司令,是陳先瑞中將。
而韓先楚,成了上將。

消息一出,有人私下議論,“他干的仗,不比韓少吧?”
“靈陜是他帶的,陜南根據(jù)地是他守的,他還帶著舊軍人翻了身……”
議論傳到上邊,毛澤東的批語寫得不多,只有一句:“此人特殊,處理從簡。”
很多年后,有人說,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為了避嫌,陳先瑞的履歷太干凈,太特殊。

他從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主將”身份,每一場仗都帶著副職頭銜,干著主官的活。
他沒進過東北野戰(zhàn)軍,也不是四野主力,打的是別人不想管的偏遠地帶,但沒人敢說他打得差。
1948年,他帶38軍轉(zhuǎn)戰(zhàn)陜南,任務(wù)是建立根據(jù)地,毛澤東親自定的目標:“三萬平方公里,半年建制,七縣控制。”
那是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數(shù)字。

敵軍在那兒扎根十幾年,地方勢力復(fù)雜,山匪、還鄉(xiāng)團、地方保安團混雜,糧食進不去,兵源也沒有。
他沒打正面仗,他帶兵繞山,切斷糧道,掐斷聯(lián)系,他不打大仗,專打要害,三個月,敵人自動后撤。
建立根據(jù)地的時候,他只用了一句話:“吃飯的地盤,要自己打出來。”
1949年建國,38軍被調(diào)入陜南軍區(qū),他不再帶兵,但留下了一整套舊軍改造機制。

他不談理論,只談紀律、訓(xùn)練、仇恨與勝負,他從未出現(xiàn)在中央拍照集體中,沒寫回憶錄,沒接受采訪。
只有在38軍原老兵紀念會上,有人寫下一句話:
“如果沒有陳副軍長,我們今天不敢抬頭說話。”
特別聲明:以上內(nèi)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nèi))為自媒體平臺“網(wǎng)易號”用戶上傳并發(fā)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wù)。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河南
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