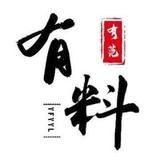1965年,山西呂梁,一座沒名字的兵工廠,從地里冒了出來,誰建的,干什么,沒人敢問。

深山里的聲音
山西的深山從不安靜,風從山梁刮過,石頭掉下去半天沒回聲。
1965年,幾輛軍車突然駛進了呂梁中陽縣的水峪溝,后斗里蓋著油布,蓋得嚴,連人影都看不清。

幾百個年輕人,衣服一色,背著鋤頭和鐵鍬,在野地里扎下帳篷,連夜開工。
沒人知道他們是誰,公社干部被請去“協(xié)助”,到現(xiàn)場就被要求閉嘴、簽保密協(xié)議。
兩個月后,溝里挖出幾十個山洞,洞口朝北,洞壁用鋼筋混凝土封得嚴實,車輪軌道一條條伸進去,像要鉆進地心。
這就是9141廠,車鳴峪兵工廠。

不是唯一的,同一年,在交口的大南溝,9146廠晉豐機械廠動工;再往南,聞喜的5447廠也開始施工,掘進隊從河南調(diào)來,帶著電鉆和炸藥。
這些地方有一個共同點:遠、隱、難找,電話沒通,道路是土的,只有一條羊腸小道通向山下。
“靠山、分散、隱蔽”,文件里就這六個字,誰問多了,就被調(diào)走。

冷鐵皮下的熱血
車鳴峪的9141廠有1000多人,開工那年冬天,山上下了五場雪,溫度零下二十,職工住在工棚里,煤炭靠馬馱,吃飯靠鍋灶。
廠區(qū)就在山洞里,七個主洞、十二個支洞,用炸藥一點點炸出來,土裝筐里背出去。

每晚八點,洞里鐵錘聲、機器聲像在地下打雷,男工敲模具,女工組裝彈殼,通風靠簡易風扇,灰塵嗆得嗓子冒煙。
有人暈倒,就拖出去灌點紅糖水,再送回來。
“一小時一千發(fā)。”這是車鳴峪每條生產(chǎn)線的定額,1969年試產(chǎn),1970年正式投產(chǎn),第一年就交了數(shù)百萬發(fā)7.62毫米步槍子彈。
那時候的車鳴峪像一座地下城市,白天不準拍照,晚上有哨兵巡邏,生活區(qū)離廠區(qū)五公里,隔著一座山。

山后建了小學、食堂、浴室和一個簡易醫(yī)院,醫(yī)生是從太原調(diào)來的,姓孫,看病不分班次,24小時隨叫隨到。
“廠里出事不能報,家屬區(qū)死人不能哭。”這話從廠領導口中說出時,沒人反駁,規(guī)矩寫在黑板上,貼在飯?zhí)每冢M洞前必須讀一遍。
1972年,一位名叫劉海的技工被炸藥震傷,雙耳失聰,工資照發(fā),但被調(diào)離生產(chǎn)線,沒人再見過他。
晉豐機械廠的情況類似,但任務不同,那里不產(chǎn)子彈,產(chǎn)工具、模具、量具,零件尺寸精度要求0.01毫米。

工人多數(shù)是從東北調(diào)來的老技師,講究細致,工具間有暖氣,有一次廠房著火,工人不跑,死命地搶設備。“這玩意壞了,前線的火炮就繃不準。”
這些人說話少,干活狠,不喊口號,只看指標。
再往南的5447廠,是坦克穩(wěn)定器的生產(chǎn)基地,廠區(qū)小,要求高。
1975年夏天,一批新產(chǎn)品試驗失敗,全廠停工三天,重新測繪。

測試員姓鄭,瘦,戴眼鏡,三天三夜不出辦公室,眼睛紅得像兔子,第四天重新裝配,一次通過,那天晚上,他喝了一斤白酒,什么都沒說,回宿舍就睡了。
這些廠子,有一種特別的氣味,鐵、汗、油、藥味混合在一起,混得咸,混得燥。
夏天熱得蒸人,冬天凍得掉皮,沒空調(diào),沒熱水,嘴里只管“完成任務”。

“三天三夜熬過去了,命還在,工件也合格。”這就是榮譽。
每到月底,生產(chǎn)任務完成,廠區(qū)廣播才響,“九一四一完成任務,優(yōu)等品98.7%,準時交付。”聲音大,傳得遠,山那頭的狗都吠。

斷裂與沉默
1985年,9141廠被下了調(diào)令,任務暫停,設備打包,整體搬遷。
搬去哪里沒人說,工人排著隊領調(diào)令,領完走人,不許打聽,老廠長只說一句:“任務完成了。”

山洞空了,鐵軌銹了,機器拆了一半,另一半被留在原地,有人試圖帶走,但太重,留著更省事。
工人宿舍的門上掛著鐵鎖,鑰匙沒人管,生活區(qū)的小門塌了一角,醫(yī)院的床被老鼠啃了腳。
廠房沒關窗,風進來,刮得響。
三個月后,整座車鳴峪變成了一片廢墟,不是炸了,也不是拆了,只是沒人再回來。
5447廠的結局沒那么“體面”,早在1980年就傳出要“合并”,領導開會,工人不信,設備用得太久,零件精度再怎么修都達不到要求。

有人想把老式數(shù)控機床改成民用銑床,但成本太高,根本沒人收。
1983年初,廠區(qū)斷電,供電站停轉(zhuǎn),家屬區(qū)照明靠煤油燈,職工們用木板封住門窗,貼上“閑人免進”的紙條,怕人來偷銅。
“我們造坦克的地方,最后連水龍頭都被擰走了。”

4500廠的結束更快,像斷了線的風箏,1987年,工人去打卡,卡鐘被拆了,辦公室空了,傳達室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話:
“停止運營,原地解散。”
當時全廠3000多人,一半不到調(diào)去了城市的工業(yè)區(qū),剩下的不是回老家,就是留下看門、巡夜。
廠里的電影院空了,臺上還掛著一張毛邊海報:“加快生產(chǎn)節(jié)奏,保障國防安全。”下面長了苔蘚。

有人說,這是計劃變了;也有人說,是技術淘汰了自己。
沒有人承認失敗,但誰都知道,“后方”這個詞,已經(jīng)不再重要。

誰還記得這些廠
三十年過去,山上的草長得比人高。
車鳴峪兵工廠的洞口被水泥封了三座,剩下的長了刺藤和狗尾巴草,洞里一黑一冷,回聲像鬼喊。

當年負責電力維護的宋老頭還在,他每年都回來看看,背一壺酒,站在洞口不說話,他說:“這地方?jīng)]人懂,我們命都是在這兒耗的。”
沒人愿意提它們,地方志上有個名字,“某廠”,照片黑白,連編號都不全。
5447廠的家屬區(qū),如今成了“危房待拆”,門上刷著“禁止入內(nèi)”,樓道里還有鍋碗瓢盆。
住戶早搬了,墻上還能看到鉛筆畫的成長標記:‘李濤,1982年,120厘米’。

有人想開發(fā),2015年,有企業(yè)想在原址建水泥廠,方案做了一半,被退回,理由是地質(zhì)不穩(wěn)、交通不便、環(huán)保難控。
“這是原軍工用地。”這句話,比環(huán)保紅線還硬。
4500廠曾被某地產(chǎn)商看中,說要做“文化旅游區(qū)”,方案提出要還原廠區(qū)場景,做“沉浸式軍工體驗”,方案沒批,沒人解釋原因。
有當?shù)毓賳T私下說:“這里死人太多,東西太沉,挖出來沒意思。”

也不是沒人動過心思,四川有個3536廠,改成了軍工文創(chuàng)園,紅磚廠房翻修成展廳,導覽員穿軍裝,游客排隊拍照,山西想學,沒人接盤。
車鳴峪有人來過,拍紀錄片,導演是個大學教授,拍了三天走了,說:“太遠,沒路,太冷,晚上沒水。”
沒人怪他,太遠是真的。那年修上山的路,是靠1000多個工人,一人背一袋石頭,一步步鋪出來的,沒人記得路是怎么塌的,只知道最后再也沒修起來。
“這地方本來就不是給人住的。”
這句話,一半是痛,一半是釋懷。

尾聲:沒人喊停
山上的工廠,沒有一個正式關門,沒人下命令,也沒人交接,就那樣,停在了時間里。
檔案封了,編號撤了,領導換了崗,只有名字,沒人敢忘。
有人說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老工人搖頭,“激情不值錢,燒完了就剩灰。”

9141、9146、4500、5447……這些編號,一旦寫進文件,就等于隱身,換了名字,抹了記錄,再也找不到歸屬。
呂梁的風還在吹,吹過那些廢棄的廠房、倒塌的車間、長滿藤蔓的禮堂和校舍。
過去講“后方”,講“任務”,講“保密”,現(xiàn)在什么都不講了,只講值不值錢。
有人站在洞口喊了一聲:“還有人嗎?”風答應了他一聲,“呼——”,完了。

他笑了,罵了句臟話,扭頭下山。
沒人再喊停,也沒人再開工。
山知道,洞知道,槍聲停的那一刻,工廠就成了記憶。
特別聲明:以上內(nèi)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nèi))為自媒體平臺“網(wǎng)易號”用戶上傳并發(fā)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河南
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