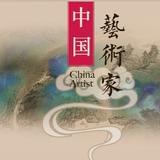韓羽
(1931—)
中國著名畫家、評論家、漫畫家
山東聊城人
當(dāng)代老一輩藝術(shù)家
現(xiàn)任河北省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會名譽會長
反常合道
讀齊白石的畫,最快意者莫過于一驚一乍:“嘿!竟然還可以這么畫哩。”
比如《秋聲》,個頭大小一模一樣的兩個蛐蛐緊緊并排在一起。誰敢這么畫?我連想都沒想過。因為畫畫兒的人都知道,畫中的形象最忌“重復(fù)”,如是一個樣兒,就成了《祝福》里的祥林嫂叨念阿毛了。

齊白石 秋聲 紙本設(shè)色
再看雞雛,《玉米雛雞》中的兩只小雞不也個頭大小一模一樣地緊緊并排在一起。齊老先生一而再之,情有獨鐘乎?
實際上蛐蛐或是小雞曾否緊緊并排在一起過?誰也沒有留過心。忽然從畫上看到了,能不多瞅上幾眼,能不思忖思忖,作畫最忌諱的“重復(fù)”,在這兒反而逗人玩味,真真吊詭也。

齊白石 玉米雛雞 紙本設(shè)色
畫畫兒干什么,依我說畫畫就是“玩”,是盡情盡興地“玩”,是物我兩忘地“玩”,是充滿了愿望與想象地“玩”。可以推想,齊老先生也是以“玩”的心態(tài)作畫,比如他拿畫筆引逗那蛐蛐那小雞,靠近些,再靠近些,像一對親密的小伙伴多么好,以此愿望之小生物,赤子之心也,而“緊緊并排在一起”不亦“親密無間”乎。
發(fā)乎筆端者,雖不是真實的事(蛐蛐、小雞不可能有孩子一樣的心思),但一定是真情的事(“緊緊并排在一起”定當(dāng)意味著“親密”)。有悖于事理,卻合于情理,變無情為有情,點鐵而成金,其蛐蛐、小雞乎。
作畫有三要,直觀感覺,悟?qū)νㄉ瘢硎觥G皟牲c略而不談,只說“表述”。就《秋聲》《玉米雛雞》來看,確切地表述出了畫意的恰恰是不忌生冷的無法之法。說句土話是歪打正著,說句文詞是蘇東坡贊柳宗元詩的一句話:反常合道。
“道”,恍兮惚兮,至玄至微,言人人殊。就“形而下”言之,不妨謂為人情世事之理。“反常”則是方循繩墨、忽越規(guī)矩。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反常”往往更切中肯綮,更接近事物的本質(zhì)。

韓羽 鐘馗 紙本設(shè)色
誤讀之趣
白石老人筆下的小生物,往往像似孩子,比如這幅畫里的小魚兒,歡快得活蹦亂跳,甚至有點兒做作了。道是為何?原來是為了向河岸上的小雞表示“其奈魚何”,用孩子話說:我不怕你!
小雞不會浮水,可望而不可即,小魚怕從何來?且看這些小雞,毛茸茸,瞪著小眼的驚詫樣兒,像極了啥都不懂啥都好奇的小孩兒,似乎聽到了它們的嘰嘰聲。“這是什么?”“這是蟲蟲。”“蟲蟲不是在草里的么,為什么在水里?”“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其實小雞是好奇,是小魚誤會了。可又正是由于這誤會,才有了戲劇性,逗得我看了小雞看小魚,看了小魚看小雞,看了笑,笑了看。
這應(yīng)說是“誤讀”,其實白石老人作畫的原意并非如此。且看跋語:“草野之貍,云天之鵝,水邊雛雞,其奈魚何。”是替小魚出一口氣的。同時又似乎還有一聲嘆息,是白石老人的:亂兵、土匪,搶糧、綁票,老百姓東藏西躲、顛沛流離,亂世人不如太平犬,更不如這河中小魚也。很明顯,是借小魚這“酒杯”,以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哀人復(fù)自哀之。而我又看又笑,當(dāng)樂子了。陰錯陽差,不吊詭乎,寫以志之。

齊白石 雛雞小魚 紙本設(shè)色
俗得那么雅
齊白石畫《谷穗螳螂》,題跋曰:“借山吟館主者齊白石居百梅祠屋時,墻角種粟,當(dāng)作花看。”耐人尋味之“味”,不離文字,不在文字。文人雅士,有愛梅者,有愛蓮者,有愛菊者,有愛蘭者,似未聞有以谷“當(dāng)作花看”者,即種谷之農(nóng)民雖愛谷亦未聞有以“當(dāng)作花看”者。
由此,使我想起多年前寫的一篇小文:
“墻角處,枝葉掩映中一綠油油肥碩大葫蘆,我們幾個老頭兒閑扯起來。有的說:‘這多像鐵拐李背著的盛仙丹的葫蘆。’有的說:‘《水滸傳》里林沖的花槍挑著的酒葫蘆就是這個樣兒。’有的說:‘這是齊白石的畫兒上的。’有的說:‘從書本上看到的,一個和尚說:葫蘆腹中空空,不像人滿肚子雜念,浮在水上,漂漂蕩蕩,無拘無束,拶著便動,捺著便轉(zhuǎn),真得大自在也。’過了兩天,再去一看,葫蘆沒了。問種葫蘆的老漢,他說:‘炒菜吃了。’”
我們幾個老頭兒談?wù)f葫蘆,說句土話,叫閑扯淡;說句文詞,叫欣賞,甚且有了點兒“審美”味兒了。只那種葫蘆老漢眼中,葫蘆就是葫蘆,是吃物,炒菜吃了。

谷穗螳螂 齊白石 紙本設(shè)色 117×40.5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白石老人將谷“當(dāng)作花看”,就關(guān)乎我們慣常說的“審美”了。本不是花,而“當(dāng)作花看”,當(dāng)必尤其有趣,趣生何處?老人沒有細(xì)說,不好妄自揣摸。既然我們幾個老頭兒的閑扯淡也有“審美”味兒,那就再說說我們。

齊白石 鐵拐李
第一個老頭兒,一瞅見葫蘆,立即想起了記憶中的仙人鐵拐李背著的盛仙丹的葫蘆,于是葫蘆上有了鐵拐李的影兒,想當(dāng)然地這葫蘆似乎也就有了點兒“仙氣”了。
第二個老頭兒,沒聽說過鐵拐李,卻讀過《水滸傳》,知道火燒草料場。一瞅見這葫蘆,立即想起了林沖買酒用的那葫蘆,于是這葫蘆上就有了林沖的影兒。盡人皆知林沖是水滸英雄,想當(dāng)然地這葫蘆也就有了點兒“豪氣”了。

齊白石 葫蘆
第三個老頭兒,喜歡看畫兒,知道齊白石畫過葫蘆。可惜的是他沒學(xué)過繪畫技法,不懂筆墨之趣,只能說出一句“這是齊白石的畫兒上的”。

韓羽 三個和尚 紙本設(shè)色
第四個老頭兒提到的和尚,一眼瞅見了葫蘆,那葫蘆的“腹中空空”的“卯眼”,恰好適合了他的人生哲理的“榫頭”,“真得大自在也”,想當(dāng)然地這葫蘆也就有了點兒“逸氣”了。
這就是審美,這就是因人不同而“審”出的不同的“美”。
“美”是客觀存在抑或是主觀感知?蘇軾有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借桑說槐,似無不可。

齊白石 玉米蟬
審美之極致,就是古人說的“神與物游”“物我兩忘”。白石老人的以谷“當(dāng)作花看”,就是審美之極致。描述審美之極致者,辛稼軒有詞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yīng)如是。”
特別聲明:以上內(nèi)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nèi))為自媒體平臺“網(wǎng)易號”用戶上傳并發(fā)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wù)。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山東
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