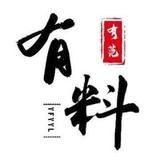明面上,兩個女人微笑碰杯,一方是英聯邦女王,一方是美國第一夫人。
可杰奎琳回國后卻私下放話:“她只是個平庸乏味的中年婦女。”真有那么大怨氣?她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兩位女人,兩種命運
1961年,冷戰正熱,美蘇對抗,間諜橫行,歐洲處于美國“反共鐵幕”計劃的戰略延伸中。英國,雖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國,但在美英關系中還保有一絲老牌大國的尊嚴。
新上任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英俊、年輕、雄心勃勃,急需借助大西洋彼岸的王室符號,為自己樹立起一種“與世界共治”的姿態。

這一次訪英,本來就是為了秀場。
杰奎琳·李·鮑維爾,比丈夫小12歲,生于紐約上東區,家境優渥,從小學習法語、歷史與藝術。
她不是政治人物,但她比政客更懂得如何“贏得現場”。她嫁入肯尼迪家族,成為總統夫人時只有32歲,卻已經是紐約媒體封為“全美最優雅女性”的時尚標桿。
她懂得如何走路,如何說話,如何穿衣,甚至懂得何時不說話。
而倫敦的白金漢宮里,伊麗莎白二世早已即位近十年。1952年,她在父親喬治六世病逝后繼承王位,當時才25歲。
她勤勉、沉穩、嚴謹,說話聲音輕緩,衣著中規中矩,幾乎從不表現情緒。王室對她的要求只有兩個字:無懈。

這兩位同齡女人,一個活得像場秀,一個活成制度。
可誰也沒想到,正因為“太像”,她們反而不來電。

一場訪問,一桌不自在的晚宴
1961年6月,肯尼迪夫婦抵達倫敦,白金漢宮為他們安排了一場不算國宴、但足夠規格的晚宴。
按理說,第一夫人該高興,這是與女王同席的榮耀,許多人求都求不來。可杰奎琳的表情,早在出發前就已經寫滿了挑剔。

她的第一條要求,讓妹妹李·拉齊維爾和妹夫波蘭王子斯塔尼斯瓦夫·拉齊維爾一同出席晚宴。
英王室一貫講究血統與禮儀,最忌諱的就是“離異者”。李是二婚,王子是三婚,這種組合若是出現在白金漢宮正式晚宴上,會讓英國貴族圈“看笑話”。
王室最初是拒絕的,哪怕杰奎琳再怎么央求,照例規矩不能破。參考當年女王妹妹瑪格麗特公主,因為愛上一個離婚軍官,差點和王室鬧翻的前車之鑒,工作人員都緊張。
可女王最終讓步了。
為什么?因為這場晚宴不是“國宴”,只是“總統級社交晚宴”,不具備國家儀式性質。換句話說,王室妥協了,但保住了體面。李夫婦出席了,但英國媒體并沒有刻意宣傳。
這本該算是給足了面子。
可杰奎琳不滿足,她接著又提出另一個請求:要單獨見瑪格麗特公主和瑪麗娜王妃。

這回王室沒有再讓步,私下見面?無日程安排、無儀式陪同、還不是國家官員身份?這在王室規范中是“非正式接觸”,一律不能搞。更何況瑪格麗特公主脾氣不小,不會輕易配合這種突發“訪談”。
杰奎琳覺得自己受了冷遇,在她看來,自己是全美偶像,是時尚風向標,王室應該高看一眼才對。
可對伊麗莎白來說,美國總統夫人只是“總統的夫人”,而英國王室,不論是公主還是女王,從來不為時尚、也不為娛樂圈讓位。
真正的“劍拔弩張”,出現在晚宴當晚。
宴會設在白金漢宮最負盛名的宴會廳,紅毯與金壁交錯,仆從穿著燕尾服遞上銀器餐具,典雅得像走進了19世紀的畫框里。所有人都在等,看兩個女人如何打招呼、如何碰杯、如何微笑。
當兩人同框,空氣幾乎凝固了。
杰奎琳穿著淡藍色一字肩長裙,質地柔順,線條干凈,法式高貴中帶著一點美式自信。她知道攝像機在對面,于是每一個轉身都有設計感。

而伊麗莎白,穿著深藍色吊帶長裙,搭配皇家藍寶石項鏈,佩戴那枚象征英格蘭的胸針。她沒有設計轉身動作,只端著杯子,點頭微笑,規矩得像一場宗教儀式。
顏色撞了,藍配藍,剪裁卻是兩個世界。
媒體注意到了,也不客氣地做了對比,英美報紙次日頭條照片里,兩人并排站立,一方是“自由與時尚”,一方是“莊重與權威”。
在杰奎琳眼里,這是她“贏了”。
可女王看得更清楚,晚宴進行中,她找了個輕松的話題:“你剛從加拿大回來吧?旅程辛苦嗎?”
杰奎琳沒察覺語氣,直接嘆氣道:“在公眾前露面實在太累了,真希望有點私人時間。”
女王點頭:“時間久了你就會學會,變得狡黠一點,也就不會那么累了。”
這一句,說得輕,卻像刀子。

伊麗莎白在提醒她:你只是“政治陪襯”,但我是一國君主,你可以用魅力轉移焦點,我得用身份穩定王國。
當時沒人注意到這段小對話,可杰奎琳回到華盛頓后提起時,語氣里透出一絲不甘。
她說:“我沒想到她會這么居高臨下……仿佛我只是個插曲。”

冷場背后的暗涌
宴會結束后,英國王室很快恢復了日常,女王沒有再提這件事。可在杰奎琳心里,這頓飯吃得不舒服。不是因為菜不好吃,也不是因為安排不周,而是覺得自己被輕視了。
她始終記得,自己提出的那些“合理請求”,幾乎都遭遇冷處理。而女王的回應,也并非表面上的客氣與得體,而是透著一股“客人就該守規矩”的冷淡。

從華盛頓回國后,她在一次朋友聚會上終于忍不住抱怨起來:
“白金漢宮就像個破舊的鄉下小旅館,連地毯都松松垮垮,房間像1930年代的療養院。”
這句話,很快傳開。
杰奎琳沒有意識到,美國媒體正在將她神化,而她的任何評論,都會變成政治解讀。
她繼續說了更多:
“她那身打扮……頭發像頭盔一樣死板,裙子顏色總是那幾種,完全沒創意。”
還有一句更刺耳的話:“她只是一個平庸乏味的中年婦女,既不幽默也不有趣。”
這些話本是朋友間的閑談,但在那個時代,名人社交圈早就是半個“情報機構”。很快,一些記者聽說了這番評價,并在隨后幾年以“匿名消息源”的方式進行暗示報道。雖然沒點名,但每個人都知道說的是誰。

而更讓王室“掛不住臉”的,是杰奎琳對女王婚姻生活的嘲諷:
“她和菲利普親王看起來根本不像夫妻,一個像老師,一個像警察,他們之間沒有火花。”
火上澆油的是,美國國內對杰奎琳這些話并沒有太多批評,反而有媒體調侃:‘或許她說出了所有女人的真實感受。’
英王室沒回應,這是他們一貫的風格:不解釋,不辯解,不追究,但冷處理并不意味著不在意,實際上,伊麗莎白二世知道得一清二楚。
她沒有公開表示任何不滿,只是繼續在年度圣誕致辭中保持優雅。而身邊人透露,她曾對幕僚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尤其是第一夫人。”
這一句,分量很重,不是反擊,是框定立場。
可杰奎琳沒收住。

她開始在更多場合提及女王,說“她太古板”“太死氣沉沉”“不像個現代女性”,這在美國聽起來像八卦,在英國卻被視為外交無禮。
那年秋天,英國《每日郵報》發表一篇評論文章,用極其委婉的筆調寫了一段話:“時尚與風范,并不總等于教養。”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在回擊杰奎琳。
雙方的關系其實早就偏離了外交軌道,變成了兩個風格不同的女人之間的“審美權之爭”。

時間,終究替女王贏回了體面
時間往后推一年,肯尼迪遇刺,震驚全球。那天,杰奎琳穿著粉紅套裝,站在血泊中的林肯轎車里,面無表情,她的堅強,贏得了全世界尊重。
英女王得知噩耗后,立即下令白金漢宮和其他英聯邦政府建筑降半旗致哀。她還罕見地下令威斯敏斯特教堂敲鐘哀悼,這是英國僅有幾次對外國領導人進行此類禮遇。

她沒說一句批評杰奎琳的話,也沒有冷落。
1965年,杰奎琳應邀再次訪問英國,這一次,女王沒有安排宴會,而是單獨請她在溫莎堡吃午餐。那頓飯沒有媒體、沒有貴族、沒有攝影師,只有兩個女人、兩份牛排、一個小時的沉默和寒暄。
女王主動打開話題,說起了小約翰·肯尼迪的教育,說起杰奎琳如何帶著孩子度過悲傷。
杰奎琳沒說太多,這場飯局被外界稱為“女性之間最沉默的理解”。
從那之后,兩人再沒有任何負面交集。
而關于那句“平庸乏味的中年婦女”的傳言,也被英國皇室“無聲掩埋”。
到了21世紀,影視劇《王冠》播出,觀眾開始重新理解伊麗莎白女王年輕時所承受的責任與壓抑。她的穿衣風格,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冷靜處理沖突,都被現代人看成一種“古典力量”。

而杰奎琳,雖然依舊被稱為“美麗象征”,但她的情緒化、易怒與對權力審美的執著,也開始被更多人質疑。
有人說:她太在乎被關注,卻忽略了權力背后的約束。
還有人說:她羨慕女王,但從來不敢承認。
1962年,杰奎琳再度訪英時,已不復當年的張揚,而女王依舊是那個淡定端坐的女人,語速慢,句子短,卻滴水不漏。
那個曾被她稱為“平庸中年婦女”的人,在幾十年后成了整個英聯邦最后的精神支柱。
杰奎琳1968年再婚,嫁給希臘富豪奧納西斯。離開了政治,也離開了時尚神壇。女王仍然穿著那套大地色調的格紋套裙,繼續接見政要,巡視醫院,握著工人們的手。

她們最終各自老去。
一個活在閃光燈里,一個藏在文件堆后。
而那一句帶刺的話語,沒能毀掉女王,反而襯出她的沉穩,真正的尊嚴,從不靠評價撐場。
參考資料:
《杰奎琳·肯尼迪:歷史中的第一夫人》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河南
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