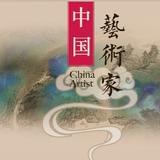傣族宣傳員玉軟
63cm×45cm
紙本設色
1978年
我經常聽到這種說法,到生活中去寫生、收集創作素材,如果要畫得具體、豐富,最好用鉛筆或炭筆,不宜用毛筆。意思就是說,如用毛筆寫生就容易把形象畫得粗糙、簡單,無法細致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于是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耍筆墨可以,但作為形象素材則參考價值不大。我對這種意見實在不能同意。
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地看。毛筆固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優越性是主要的。對它的優越性缺乏認識,主要是由于缺少實踐。

舞蹈家石鐘琴
68cm×45cm
紙本設色
1982年

白孔雀
68cm×45cm
紙本設色
1980年
將寫生、默寫與構圖結合起來訓練是中國畫傳統的學習方法,如果要學習傳統的精華,這個經驗是不可忽視的。五代黃筌的《寫生珍禽圖》已體現出筆墨與形象的完美統一。當我們看到他筆下描繪的無論羽毛豐滿的小鳥還是翅膀透明的鳴蟬,不能不為我們祖先當年創造的毛筆這一獨特的工具而感到自豪。中國人物畫既有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目識心記”的記憶畫法,也有對景取神的寫生畫法。清代任伯年曾在一寫生肖像畫上題有作畫過程:畫了一半,油燈滅了,迅速再燃紙照明,紙燃盡,像也畫好了。可見他毛筆寫生之熟練。近代嶺南畫派之所以被認為有創新精神,也是與其重視寫生分不開的(寫生中也摻入西法)。“因循守舊”是傳統之糟粕,學習方法上的致命傷是將藝術“源”與“流”的關系顛倒了。而面向生活的寫生,對沖破形式主義的枷鎖是具有積極作用的。只要看一看關山月、黎雄才兩位老畫家從青年時代起積累下的數以千計的毛筆寫生畫稿,就不難理解這種辛勤的實踐對他們之后在國畫創新上的成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了。
毛筆寫生的特點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將對生活的強烈感受通過筆墨——傳統的藝術語言充分地表達出來。使用毛筆的難度在落筆不好改,落筆就成定局。是否能達到用筆的高度準確性,首先取決于對描繪對象認識的深刻性;只有把握對象的本質,才有可能產生可靠的感受,也才有可能產生果斷的筆墨處理。所以,通常我們贊美筆墨洗練概括的中國寫意畫,就是由于作者不但把握了對象的形,更重要的是把握了對象的神。最要不得的是,“毫發不差,若鏡中寫影,未必不木偶也”。古代畫家把人物畫叫作“傳神畫”,就是強調一個“神”字,主張“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我認為,學習傳統不能只學筆墨,而首先要學習前人如何將生活現象創造成藝術形象的經驗,將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印象與想象、研究表現內容與探索筆墨技巧在寫生的過程中緊密地統一起來。

滇南采風
138cm×69cm
紙本設色
1979年

藏族牧羊工昂久
67cm×45cm
紙本設色
1980年
毛筆寫生的難處也正是它的好處,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傳統毛筆工具的優越性。一支毛筆千變萬化,從毫尖到筆根,從最實的焦墨到虛幻的淡墨,從柔軟的質地到堅硬的質地,猶如音樂中從最低音到最高音豐富的節奏感,利用這一切有利因素去傳對象的“神”。毛筆寫生應該是充滿激情的,是有立意、有取舍的,比看到的對象的特點更集中、更強烈。即使是畫瞬間即逝的舞臺速寫,也不例外。困難不全在落筆即成定局的線條不容易追上快速變動的姿態,而往往難在當機立斷的剎那間才能表現人物的特點。這個“取”還包括衣紋的處理:舍棄煩瑣的,取其最關鍵的衣紋線條。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說是理解重要還是感覺重要了,只能說是“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1962年的八一建軍節前后,我曾與京劇團的同志朝夕相處,聽多了,看多了,對劇情及表演有了較深入的理解,如此使我很容易找到哪個動作最能體現穆桂英的英雄氣概。
于是,我選定唱到“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時穆桂英手托金印這一瞬間的亮相,用迅速而肯定的白描線條記錄了下來(因白描的傳統形式與古裝人物的內容容易協調一致)。想要用描繪的動作體現唱詞的內容,如果不熟悉劇情,就是感覺再好的人也是做不到的。又如另一幅日本舞蹈的速寫,也有它的特點,日本舞蹈的節奏感特別強烈,動作較為緩慢但明確有力。所以,我用毛筆速寫時除了把握舞蹈的動感,還注意運用線條輕重頓挫的變化來表現強烈的節奏感,這后來成為我創作《歡慶驅鬼勝利舞》時筆墨變化的重要依據。

礦山新兵
130cm×94cm
紙本設色
1971年

黑河女牧工
68cm×45cm
紙本設色
1980年
人物寫生時為了加強人物的本質,與山水畫家寫生時重新安排山河一樣,人的構圖處理也可以運用調度與想象。我在寫生《藏族青年阿珍》時,感覺他橫坐在長板凳上的動作極似騎在馬背上的動作,于是,我將凳子想象成馬背,背景的雪山也是虛構的,因為這樣可以使人物與環境協調。又如畫《公社書記》時,也是在室內寫生人物的,景是后來對照秧田補寫的,這樣通過寫生的真實感來加強描繪對象的感染力。由此可見,毛筆寫生可以與構圖練習結合起來訓練,這樣的寫生就具有創作的因素。從生活到藝術的升華過程,可以從鄭板橋談畫竹的經驗得到啟示。他說,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他很好地說明了眼、心、手三者的辯證關系,與機械地模擬對象的自然主義是格格不入的。
在毛筆寫生的過程中,不同的對象必須尋找不同的筆墨去表現。筆墨的精神與對象的傳神關系非常密切,如我用結實明朗的筆法去表現陽光下的僾尼民兵,而用另外一種柔和的筆法去表現樹蔭下溫柔的傣族少女(我嘗試用先著色后勾線的特殊處理方法來表現自己當時的感受)。當我畫“蘇大眼”時,完全拋棄了常用的明暗皴擦法,而完全用線條去表現他滿臉紋路的特點;畫老飼養員郭大伯時,我用明確硬朗的線條去表現他爽朗而又幽默的性格,左邊用濃墨畫的斜披著的上衣打破了畫面的平衡,也加強了其豪放、不拘小節的性格特征。“夫神之所以相異,實有各各不同之處,故用筆亦有各各不同之法”,就是這個道理。

夜深人靜
44cm×59cm
紙本設色
1980年

機織女工
62.5cm×45cm
紙本設色
1980年
用毛筆寫生去收集創作素材的優越性也是別的工具所不具有的,因為毛筆畫的素材不僅能作形象參考,還能作筆墨處理參考。如為了創作《紅日照征途》一畫中毛主席身邊的湖南農民的形象,我去湖南文家市等地畫了七八張同樣角度的青年農民毛筆寫生,這些素材不僅給我提供了人物形象的參考,而且還提供了如何用筆墨去塑造形象的筆墨技法參考。如面部五官用線的變化,表現肌肉的皴擦,以及黑上衣領的沒骨法與藍包袱的勾線法之對比,這些筆墨技法都是從面對描畫對象時的即時感受中提煉出來的,故筆墨變化一氣呵成,比較自然。這些有利因素在我創作正稿時幫了不少忙。
當然,毛筆寫生有一定的難度,但我認為關鍵在多實踐,熟能生巧。毛筆這一工具好像一匹烈性的馬,你越怕它,它越欺你;如果你征服了它,它就是一匹最聽使喚的好馬,任你自由馳騁。

新疆藝校女學生莉莉
51cm×42cm
紙本設色
1980年

繅絲女工
46cm×34cm
紙本設色 1963年

塔吉克族老太太
63cm×46cm
紙本設色 1980年

評劇演員新鳳霞
65cm×48cm
紙本設色 1981年

作家楊沫
65cm×45cm
紙本設色 1983年

越劇演員傅全香
66cm×46cm
紙本設色 1983年

反彈琵琶
69cm×69cm
紙本設色 1990年

小提琴手
70cm×48cm
紙本設色 1993年

新疆舞
69cm×46cm
紙本設色 1994年

68cm×46cm
紙本設色 1985年

唐舞
69cm×46cm
紙本設色 1993年

恒河畔的腳鈴聲
82cm×48cm
紙本設色 1987年

翻騰的云
80.5cm×68cm
紙本設色 1991年

小天鵝
68cm×46cm
紙本設色 2006年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山東
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