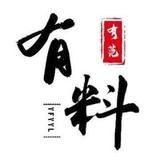張作霖,中國近代史上唯一一個被日本官方列入“征信黑名單”的軍閥。
他借走數十億日元,一分不還,還公開放話:“我憑本事借的錢,為什么要還?”
這不是玩笑,而是一場精心布局的政治騙局,他到底是真“老賴”,還是民族英雄?

“空手套白狼”:不是你蠢,是我騙得專業
1907年,張作霖還是個旅長,他知道一個道理:槍桿子里出政權,可光有槍不行,還得有錢。
有了錢,才能買到更多槍,東北地廣人稀,想成事,必須得外援,俄羅斯和日本,是那時候最主要的金主。

他不傻,他知道日本人不是好心,可他賭他們貪心。
1920年代,日本對華貸款逐年上升,其中絕大多數流入東北,張作霖的東北軍成了最大“借方”。
據當時日本《外務省年鑒》記載,張作霖在職時期,從日本獲得貸款金額約10億日元,這是當時中國財政部年收入的四倍。
他怎么做到的?

第一步,抵押。
他說得堂皇,拿出奉天城地契、鐵路線使用權、甚至礦區開采權,一一列給日本人看,抵押合同寫得清清楚楚,蓋章、落款,樣樣齊全。
但到了貸款到賬那一刻,立馬變臉,奉天?我現在叫沈陽了,地名換了,你合同還有效嗎?
鐵路?剛被國有化,權不在我手了。
礦區?你寫的坐標不對,挖不到的。

第二步,簽名。
日本人最早發現貓膩是在1923年,當時他們催債無果,派人查合同,才發現很多貸款文件上根本沒有張作霖的正式簽名。
最典型的是“閱”字簽名,所謂“閱”字,就是看過,但不是簽署。
而且更狠的是,一些合同上的“簽字人”,根本不是合同簽署日那天的在任官員。
比如,楊雨亭出任東北財政總長的時間是1922年5月,但貸款合同卻寫著1922年3月他已簽署,日本人大怒,卻無可奈何。
張作霖的說法更絕:“我沒簽啊,我手下愛干啥干啥。”再說了,“沈陽不是奉天,合同自然失效。”

第三步,拖。
日本人派了幾十名官員來東北催債,張作霖從不拒見,但也從不還錢,他用一招:“買槍了。”
“你給我錢,是讓我打仗的,我也打了,子彈都打光了,還錢?錢早沒了。”
他還說:“你想不想蘇聯入侵東北?我是在替你擋子彈。”
這話日本人聽著別扭,但也不能反駁,張作霖的“太極戰術”,讓整個日本外交體系陷入僵局。

最滑稽的一次,是1926年,一位日本財政使者怒吼:“你違約在先,必須歸還貸款!”張作霖只回了一句:“你貸款給一個不講信用的軍閥,本身就有問題。”

政治游戲:不是不還,是不能還
張作霖不是不想還錢,他是根本不能還,還了,就沒了底氣。
東北是他的根,他清楚,日本人一旦控制債權,就會伸手要地,他還過一次,代價極大。

1921年,張作霖因戰事緊張,被迫將大連灣局部港口管理權交由日本代管,當時只是為了3000萬日元短期軍費貸款,他本以為幾年后可以收回來。
結果5年后,他去收,港口已被日本關東軍圈地,駐軍進駐,變成軍事要塞。
那一刻他明白一件事:日本人不是要債,是要地,此后,他徹底轉變策略。
錢可以借,地不能給,軍事顧問可以來,但不能插手軍權,技術人員可以請,但合同必須寫“臨時聘用”,所有合同都要有出口。
有日本人問他:“你一直拿日本的錢,不擔心日本翻臉?”

張作霖說:“你們的賬是跟賬本算的,我的賬,是跟天下人算的。”
這句話被后來的張學良記在日記里,他說:“我父親看起來精明,實則剛烈,他嘴上講利益,骨子里是硬的。”
日本人不是沒想過硬來,早在1927年,就有日本參謀提出“肅清張作霖”計劃。
關東軍當時建議干掉他,由更“聽話”的軍閥上臺,這個人選一度是郭松齡。

但張作霖的情報網早已布局,他提前把郭松齡調出,隨后秘密清除與日方走得太近的參謀十余人。
而他自己,表面上繼續“親日”,實際大搞武器自主化,最典型的是東北兵工廠的建立。
借日本的錢,建中國的槍廠,生產制式步槍、手榴彈、甚至火炮。
“以彼之資,還彼之債。”這不是網絡段子,是當時奉天陸軍學校的口號。

東北獨立:借日制俄,借俄制日
張作霖并不是一味親日,他一直在日俄之間來回橫跳。
1918年,俄國內戰爆發,紅軍與白軍廝殺不休,遠東勢力混亂,東北邊境頻繁被侵擾。
日本見狀提出“幫忙駐軍”,張作霖表面答應,背地里卻悄悄派人向蘇聯傳話,希望以“抗日”為籌碼,獲得政治默許。

結果就是,他一邊拿日本的錢修鐵路,一邊讓蘇聯紅軍“暫駐”黑龍江邊界,以壓日本。
有次外交電文中,張作霖對手下說得露骨:“日本想要鐵路?讓他們鋪,錢也拿著,但沿線哨所,一律歸我們軍管,出了事,他們自己負責。”
這種“兩邊下注”的做法,極其冒險,卻讓他在東北站穩了十年不倒。
同時,他也深知東北民間對日本仇視極深,所以每當與日本議事結束,他總會在沈陽城門口來一段“反日表演”。

一次,他在日本人走后,當街對士兵說:“東北是咱中國人的,鬼子別想拿一寸。”周圍百姓當場叫好。
他要的不只是政權,更是人心。

“老賴”與“英雄”:歷史的雙面鏡
張作霖死于1928年6月,被炸死在皇姑屯的列車上,火車炸飛,尸體殘破,只認得出他慣戴的皮手套,殺他的人,不是仇家,是日本人。
動手的是關東軍,理由也簡單:張作霖借債不還,騙到最后,還敢拒絕交出東北控制權,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再也無法控制他了。

他太滑,太狠,太不按規矩出牌。
炸死他以后,日本以為張學良更好控制,結果徹底看錯,張學良反而倒向南京政府,宣布“東北易幟”,從此,日本在東北布局十余年功虧一簣。
炸了張作霖,東北沒拿到,貸款也收不回,成了最失敗的一次軍事干預。
歷史評價從那一刻開始分裂。
一邊,是“失信軍閥”的形象,日本外務省在1930年發布的內部文件中,專門列出張作霖為“對日金融失信者第一名”。

這份名單后來在日本民間廣泛流傳,被稱為“征信黑名單”。
另一邊,是“民族抗爭”的符號。
東北工人流傳一句話:“張大帥騙人,騙的都是日本人。”
在當時民眾眼里,張作霖雖然跋扈、貪財,但他知道“不能讓日本人拿地”,他私吞的是錢,護住的是東北。
奉天陸軍講武堂的一份舊講義中寫得更直白:“日本不是朋友,是資本家,我們用他們的錢修我們的路、打我們的仗,這是本事。”

他甚至有句話被寫進民間唱本:“我借來的不是錢,是主權的緩刑。”
雖然沒人知道他是否真說過,但這話傳了下來,那年沈陽的小報上寫:“不還債,是他的抗日方式。”

欠債不還,成了現代段子
時間過去了近百年,張作霖的“老賴史”,變成了今天中國網絡上的段子。
最有意思的是日本反詐APP“警視廳防騙通”的頭像選用了張作霖的形象。

不少用戶點開,看到的是一個胡子拉碴、穿軍服的頭像,配文:“騙錢無賴,借而不還。”
日本網友調侃:“他是我們歷史上被騙最慘的人物之一。”甚至在豆瓣有一條熱評寫著:“張作霖要是生在現在,連共享單車都借不到。”
但玩笑之外,也有敬意。
日本警視廳內部一篇教材中提到:“張作霖極度精明,對條約結構、簽署形式、抵押權屬的破壞性操作,具有極強的法律鉆空能力,是典型的金融詐騙政治化案例。”
他們氣得咬牙,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不是亂來,是策略。
中國網友反而樂見其成,一段爆火的視頻將張作霖的“貸款戰術”比作“民族金融游擊戰”。

視頻里一句話沖上熱搜:“別人靠信用,張作霖靠膽子。”
還有人寫段子:“張作霖用一支筆,一張紙,借來了一個軍隊,打沒了十個國家。”
現實世界中,這種“騙貸式抗爭”不值得推廣,但它在那個時代,是活下去的方式。
他不是民族英雄,但他做了一件事,在規則被外人制定的時候,狠狠撕破了那張紙。
在規則面前,他不是遵守者,而是干擾者。
民間的評價,比史書更真實,有東北老人說:“張大帥能吃、能喝、能騙鬼子的錢,咱愿跟著這樣的爺。”

你說他是梟雄?他說自己只是“活命的老賴”
張作霖死得很慘,但死得不冤,他早知道自己遲早會被日本人清算,他在死前幾個月,說過一句話,記錄在《張學良口述歷史》中:
“我張某人,騙鬼子錢,是拿命換的,要是給他們拿地,那我才真該死。”
這不是一句豪言,這是一個老軍閥的生意賬,只不過,這筆賬,后來被人當成了民族賬。

歷史沒有非黑即白,張作霖既是“老賴”,也是“不交地”的硬漢,他把信用當武器,把合同當棋子,玩得極限,也死得極致。
他是那個年代最不講規矩的人,也正因如此,他活得最久,死得最有聲。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河南
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