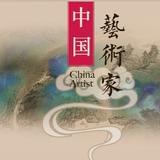他是個背著糞筐去寫生的老頭,一次又一次地撕毀自己畫好的畫的老頭;是個畫價最高賣到2個億,晚年卻只想吃煎餅,但是咬不動了的老頭;是個倔強的,注定獨行,注定傳奇的老頭

藝術界對吳冠中的評價往往容易打起來。
傳統派說他不懂畫畫,不會用筆,當然他自己也說過“筆墨等于零”,一句話打爛傳統派的大腿骨,讓人恨得咬牙 。
而喜歡他的新派人會說,你們這些人,還用筆墨來評價人家,殊不知人家畫的根本就不是中國畫。
吃瓜群眾多半表示,哎呀這個人畫的真好看,于是,吳冠中作品被印在衣服上,盤子上,還有數不清的廉價復制品掛畫,吳冠中系列的藝術衍生品,是賣的最好最多的。
他是個背著糞筐去寫生的老頭,一次又一次地撕毀自己畫好的畫的老頭;是個畫價最高賣到2個億,晚年卻只想吃煎餅,但是咬不動了的老頭;是個倔強的,注定獨行,注定傳奇的老頭。

1949年末,“留法三劍客”吳冠中、趙無極、熊秉明進行了一次徹夜長談,此后,趙無極、熊秉明繼續留在法國,而吳冠中則決定回國。這個決定,使他的命運軌跡開始變得與另外兩人截然不同。

吳冠中在法國凡爾賽宮前留影

朱德群(左)、吳冠中(中)和熊秉明(右)
獨自一人踏上歸國的旅程,想必吳冠中已對國內的艱苦環境有了心理準備,他卻依舊沒有料到,一場文革,不僅不能好好搞藝術,搞不好連命都會丟掉。
據說70年代末,吳冠中和袁運生等人夜談時抱怨了一些不平事,第二天老先生一大早去敲袁運生的門,再三叮囑說:昨夜談話沒有錄音吧?千萬不可外傳啊!此時文革已經結束,可僅僅一次夜談卻仍令吳冠中心緒不寧,可見那個時代遺留下的恐懼和壓抑有多可怖可怕。
那些歲月里,失去了創作表達的自由,吳冠中是痛苦的,可他也明白,只有先活下去,才有可能繼續畫,畫他真正熱愛的東西。他轉而開始創作更為穩妥的風景畫。

吳冠中在野外寫生
就算只有糞筐,他也要用它寫生
就像畫家中的徐霞客,吳冠中的一生,拿著畫筆走遍了中國各地。
從1919年生于故鄉宜興,到1935年轉讀杭州藝專,再到抗戰八年跟著學校師生不停輾轉于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各省,盡管飽經戰亂,卻不妨礙吳冠中在畫板和紙上記錄下了每個地方獨特的美。

吳冠中在萬源寫生
1946年,他到巴黎美術學校留學,法國現代主義油畫,讓吳冠中對色彩更加敏感。
過眼的風景,因不同地域、不同季節而被賦予不同意義的色彩,一天之內光線的明暗變化也會造成細微的色彩差別,那時的世界,在吳冠中的眼中,是他要時時刻刻去抓住的“美”,是美的靈與肉。

克勞德·莫奈《睡蓮》, 1914-15

皮埃爾·伯納德《Resting in the Garden》,1914
五十年代吳冠中回國后,不久就開始文藝整風運動,吳冠中從法國學來的人物畫被批判為“丑化工農兵”,本人也被批成了“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堡壘”。
可讓吳冠中畫革命人物畫,他也不愿意,改畫風景,成為他最合適的選擇。
此后幾十年,他大江南北去寫生。就算一度被下放到石家莊農村勞改,條件艱苦,他也不曾放棄。

1970年,吳冠中(左起第三人)下放勞動期間,與同事、學生攝于李村。
在下放到石家莊李村時,他背著當地特有的一種糞筐,裝著在村頭商店買的馬糞紙壓制的小黑板,刷上一層膠,去李村到處寫生。高高的糞筐卸下來,就成了畫架,筐里裝上顏料,連畫箱都不用了。
在糞筐上,他畫出了李村的矮屋泥墻,桃紅李白,燕子筑巢,野菊花開。
他說:“我珍視自己在糞筐里的畫、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種氣質、氣氛,是巴黎市中大師們所沒有的,它只能誕生于中國人民的喜怒哀樂之中。”

吳冠中在北碚寫生
我愛上了北京,從此南腔北調
留法之前,吳冠中幾乎都在南方度過,習慣了小橋流水人家的精致秀美,回國定居北京后,他發現周圍變成了規規矩矩的城市街道,連山水也要比南方的線條硬一些,不免單調乏味。

老北京照片

1974年夏,吳冠中全家于北京前海北沿舊宅。
但在北京生活久了,漸漸他也發現了北京的美。這里有世俗熱鬧的胡同市井,有獨立幽靜的四合院落,有莊嚴雄偉的皇家宮殿,也有大氣恢弘的北方園林,雖不如南方秀麗,卻更加氣勢磅礴……
后來他在《大江南北》中寫道:“數十年的相親相熟,不單調了,是單純,是質樸,是大氣磅礡的粗獷之美……確乎,我是一個南腔北調之人,愛上了北國的統一基調銀灰調”。

正在京郊古村寫生創作的吳冠中
所以他用屬于北方的銀灰調,畫下了這幅《京郊山村》。

吳冠中《京郊山村》
看到圍墻里的四合院,自然就聯想到老北京。木質門楣上貼著的大紅色對聯,院落中悄悄伸出的幾支粉白相間的玉蘭花,處處透著初春的生機和濃濃的京味兒。

局部
那時北京還沒有被霧霾籠罩,空氣是讓人感動的澄澈明朗,所以能夠看到群山連綿起伏,由近及遠的棕、棕藍和灰藍層次分明,一直延伸至遼闊蔚藍的天際。

局部
這幅作品可以說是吳冠中六十年代風景油畫的經典代表作。他在畫外題識:“山里人家,安于本分生活,永葆自家顏色。”
這幾句話,何嘗又不是他渴望脫離歌功頌德的主流大環境,專注于畫畫本身的心聲呢?
趙無極來了,不能喝水,因為沒廁所
1967年,文革開始,無盡的黑暗來臨。因為他的作品,吳冠中被抄家,也不能畫畫、寫作,他只能用法語搞翻譯,可書籍不能出版,文章也屢遭退稿。

吳冠中生前在螺螄殼式書房里工作
就在那個時期,他被下放到河北農村接受勞改背著糞筐去寫生,學生們都叫他“糞筐畫家”。
當時趙無極回國了一次,一定要去吳冠中家做客。可吳冠中家窮得連廁所都沒有,所以他只能勸趙無極:“你來可以,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我家里沒有廁所,喝了水很麻煩。”后來趙無極聊得興起,喝了很多紹興黃酒,只能上街找廁所。

1993年11月,吳冠中(左二)
在巴黎賽努奇博物館舉行個展
朱德群(右一)、趙無極(右二)出席開幕禮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吳冠中只有在面對風景時,才能稍被治愈,所以他熱愛風景寫生。很久以后,他接受采訪時說:“古代的畫家我不知道,現代的畫家沒有人像我寫生這么多了。”
直到1973年,吳冠中被調回北京創作賓館畫,才得以“重獲新生”。
他騎上自稱“寶馬”的自行車,馱著畫板,迫不及待地在京城四處游走,用他的話說,是:
“餓的眼,覓食于院內院外,棗樹,垂柳,木槿,向日葵,紫竹院的荷花,故宮的白皮松……均被捕捉入畫。又騎車去遠郊尋尋覓覓,有好景色就住幾天,畫架支在荒坡上,空山無人,心境寧靜,畫里乾坤,忘卻人間煩惱,站定一畫八小時,不吃不喝,這旺盛的精力,這沈迷的幸福,太難得。”
在京郊,他尋回了心底的靜謐,眼前怒放的桃花使他創作出了《春色滿園》。

吳冠中《春色滿園》
看天空中那幾抹紅暈,這大概是一個清晨或黃昏,光線較弱。一排小樹在畫面前景參差排開,歪歪扭扭,盈盈綠意和初放的花朵。
而后幾株盛放的梅花樹占據了中景,樹干粗獷剛健,很有中國寫意山水畫中的虬枝老干的筆意。梅花用的是西畫中的點彩手法,不同角度的梅花用不同色彩區分明暗,層次分明。

局部
花木簇擁下,三五行人沿著山間小道漫步走向高處的山屋,令風景動人起來。
和《京郊山村》的明快輕盈完全不同,這幅作品構圖飽滿緊湊,色彩厚重,是吳冠中介于“抽象”與“寫實”之間的作品。也許在經歷了“寒冬”后,這難得的春天,對吳冠中而言,也變得更加豐富和厚重。
他就像在山里邊選礦(寫生),邊煉鐵(創作),通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把他認為的形式美騰挪移借到了一起。
要形式,要純粹的形式!
1979年,吳冠中在《美術》雜志發表了《繪畫的形式美》一文,其中“形式大于內容”論調在美術界引起了強烈議論,此前的中國,從來沒人敢這么說。
這時吳冠中已經六十多歲,身體不好。但他仍然堅持全國各地走,去寫生。在四川烏江龔灘古鎮,他從鱗次櫛比的吊腳樓里,找到了純粹的形式美。

烏江邊龔灘古鎮

吳冠中《烏江人家》
在《烏江人家》中,吳冠中只憑借黑、白、灰三色,和長、短、寬、窄的不同形狀,就構成了“屋宇縱橫連綿,參差三萬人家”的感覺。
“街與江流抱合,房屋從右下角深入畫面,曲折前進,或呈 S 形上升,至左上角隨著一棵樹扭轉了方向,于是,沖力轉化成江流波狀之線,幾番回蕩,出了畫圖。”
吳冠中想要的,是點線面自己去歌唱。
同樣是山水,漓江與烏江的美又各有不同。下面這幅《漓江》是他在1970年代桂林油畫寫生基礎上進行的再創作。可以看出對于復雜的風景,吳冠中一直在做“減法”,不斷接近抽象。

吳冠中《漓江》
吳冠中曾多次回到故鄉宜興進行風景寫生。宜興地處太湖沿岸,被青山綠水環抱,山水草木皆可入畫,他尤其愛宜興的那片竹海,還為“竹海公園”題寫了名稱。

宜興竹海
1985年,面對萬千翠竹,吳冠中畫下了一幅極具視覺沖擊力的《竹海》。

吳冠中《竹海》
竹子的堅韌、挺拔、氣節一直是中國文人畫最愛的題材之一,但與表現文人雅致的數枝竹子不同,吳冠中這幅《竹海》,用油畫的方式表現了相當強壯的氣勢。
這樣重復、規整的滿構圖排列,加上仰視的視角,令竹海氣勢萬鈞,猶如身姿筆挺的士兵,整裝待發。
他在同年創作的《野菊花》中也這樣布局,將現實中分散的野花集中到畫面中,“擴大其威力與面積,構成座山雕式的野菊王國”。

吳冠中《野菊花》
但在《竹海》中,吳冠中所使用的色彩又具有東方的神秘、內斂。

《竹海》局部
抽象的綠色線條縱向伸展,筆刷平推出竹節,通過草綠、湖綠、翠綠、黑色的層層漸變、堆疊呈現出了強烈的節奏感。不得不說,吳冠中在具象與抽象之間達到的這種微妙的平衡,令人心折。

吳冠中在竹海寫生
線從峰巔跌入深谷,仍具萬鈞之力
吳冠中在1973年創作《長江萬里圖》時,曾與黃永玉、袁運甫、祝大年等人一同到黃山寫生,那時,奇松、怪石、云海、險峰便令他感受到了線的力量。

吳冠中夫婦在黃山寫生
他在《且說黃山》一文中寫道:“線,從峰巔跌入深谷,幾經頓挫,仍具萬鈞之力,滲入深邃,人稱那谷底是魔鬼世界,扶欄俯視,令人腿軟。谷外,一層云海—層山,山外云海,海外山,大好河山曾引得多少英雄折腰,詩人歌頌!”
在黃山,他看到了石濤的蒼莽恣肆,并由此受到啟發,畫了很多速寫。經過多年的采風與嘗試,他終于將黃山用極其凝練的點、線、面表現出來。

吳冠中 《黃山》
在《黃山石》中,吳冠中用抽象而流暢的線條勾勒出了山體,筆尖的停頓、轉折帶出了怪石的險絕,濃重的墨點抹出彎腰致敬的迎客松。

吳冠中 《黃山石》
而這幅《黃山石》更是把線條的運動感發揮到了極致。
吳冠中用奔騰曲折的細線表現出山石輪廓,灰色排筆板刷隨著線條運動,加強了在云影掩映下,山石變幻莫測的動感。

吳冠中《黃山日出》
1988年的《黃山日出》比前兩幅更為成熟。
一座主峰矗立畫面中央,高聳入云,幾何形的山石構成了主峰的山體,方與尖、疏與密、橫與直的線條與平面相互支撐出山的脊側,濃墨與淡墨的對比顯現出日出之時的明暗。
一切靜止的景物在吳冠中的筆下,似乎都添了靈動。
風景與人體可以結合,所有的藝術都可以共通
時間輾轉到90年代,吳冠中越畫越多,越畫越好,但當他回過頭看以往的畫時,不滿意的也越來越多,于是在1991年9月的一天,他整理家中作品時,竟然一口氣撕掉了200多張覺得不好的畫!

1991年秋,吳冠中在家中整理存畫,毀掉二百余幅不滿意的作品。
一張畫就是一百萬,吳冠中撕起來一點兒不心疼,他心里只想著:“讓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
下面這幅《野井(倒影)》就是吳冠中眼中“挑不出毛病的畫”。

吳冠中 野井(倒影)
井水寧靜無波,形成了光滑平整的鏡面,構成了畫面最大面積的灰色基調。水面映出井邊生長的白樺樹和叢生的雜草,或粗或細的線條打破了鏡面的單調。
雜草隨細風輕擺,在后面深綠色的襯景中顯出幽靜中的韻律,而畫面中黑、明黃、橘紅的點,更如同跳動的節拍,這是吳冠中想要達到的音樂感。
此時,吳冠中已經畫了四十年風景畫。四十年前,他因不愿意畫革命現實主義人物畫,因此轉而畫風景,而到了90年代,得益于大環境的寬松,他終于能夠重拾人體畫創作。

吳冠中《夜》(局部) 1990 年作
不過這次和他年輕時在法國畫人體已經有所不同。他自己也意識到:“追憶丹青生涯,九十年代再畫人體,重溫青年時代的夢,然而永遠無法涉足于當年沐浴的河流中去。”
步入古稀之年的吳冠中,進入了“黑色時代”。這幅人體畫《夜》的技法雖然有塞尚馬蒂斯的影子,但基調卻是幽深的、神秘的,就像吳冠中的內心,又開始偏愛悲劇的調子。

吳冠中畫人體寫生
此外,淡化了“灼燒、肉體”的感覺,吳冠中將他多年來在風景畫中積累的經驗,運用到了人體畫中。

吳冠中《老虎高原》
赭石色的線條流暢緊實,此外吳冠中拋棄了油畫中慣用的筆觸,轉而像中國水墨那樣,用不同顏色的大面積色塊延展出了肌體效果,飽滿而富有明暗變化。這種筆法,其實從《野井(倒影)》中就能看出苗頭。
吳冠中從不推崇“油畫要姓油、國畫要姓國”的說法,在當時的氛圍下,是不被人理解的。但固執如他卻也不在乎,堅持“推翻成見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創造新意境新審美,更是藝術家的身家性命。”

吳冠中《憶杭州》
就像這幅《憶杭州》,既有油畫的筆觸和銀灰的基調,又有黑瓦白墻小橋流水的東方風韻,水波的節奏感像詩,像散文,像音樂。在他的眼中,不只繪畫之間沒有界限,整個藝術范疇都是共通的。

吳冠中在江南寫生
學生辦叛徒畫展,我愿意看
但這種中不中洋不洋的風格,讓他站在了當時主流畫壇的對立面,成為了人們眼中的“怪咖”。

其實吳冠中從小就是“怪咖”,明明是理工學霸,卻鐵了心要去杭州藝專學畫畫。學了畫畫之后,他也不是太聽話的好學生。
雖然他尊敬導師潘天壽、林風眠、吳大羽、蘇弗爾皮……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他們的影子,但后來,他更愛尋找導師作品中的失敗處。他曾說:“發現了失足點,才更理解其道路之曲折艱辛,似乎也就跟著他們跋涉了探索歷程。”
水陸兼程,他學會了方法和技巧,沿途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后來成了老師,吳冠中甚至鼓勵學生辦“叛徒畫展”,學生畫得好,還不像他,這才是吳冠中樂于看到的。

吳冠中在給學生授課

1995年10月,吳冠中于香港藝術館畫展海報前。
1981年,吳冠中作為中國美術家代表團團長,赴西非訪問,途經巴黎,見到了老朋友朱德群、熊秉明和趙無極,彼時這三人已經成為享譽國際的大畫家。
聽聞在他們藝術蓬勃發展的時期,吳冠中卻在國內獨自經歷了諸多磨難,熊秉明就問吳冠中:“如果你不回去,一定走在朱德群、趙無極的路上,你后悔不后悔?”
吳冠中說:“我不后悔。我們走的路不一樣。我后來也免不了經歷各種各樣的苦難,但是到了最后看,我愿意回來,還是今天的我。”
這樣的吳冠中,注定只能一個人跨過千山萬水,然后成為獨一無二。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山東
山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