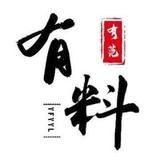左宗棠曾說鮑超“實不能統帶三千三百人”,幾年后,他卻在奏折里稱其“勇冠三軍”。
這不是打臉,這是生存,不是欣賞,而是不得不依賴,左宗棠為什么轉變態度?故事開始在他極度不信任鮑超的時候。

鮑超被看不起,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左宗棠第一次聽說鮑超,是從胡林翼嘴里,那年,胡林翼正在籌建一支突擊部隊,鮑超是首選,左宗棠不信。
“此人拙亦難轉。”左宗棠親筆寫信,字字帶火。

他嫌鮑超“行伍出身”,看不起他沒讀書,不識字,脾氣還大,更關鍵的是,鮑超治軍不講章法,軍紀像潑出去的水。
他不止一次地說:“此人必成笑柄。”
但胡林翼堅持,理由很簡單,打仗靠的是能殺人的,不是能寫文章的,左宗棠不服,還是派人盯著鮑超。
鮑超剛建軍那陣,霆軍根本不叫軍,叫雜牌,他從湘潭、衡山一帶拉來一批苦力、流民,什么都沒有。
官府不想供,百姓不敢靠,他們就在山里扎營,砍樹做帳,燒野獸吃。
左宗棠看了一眼,冷笑一聲:“草莽之兵。”
但局勢比他想象的緊,湖北失守,安徽危急,太平軍攻勢不減,清軍主力都在收縮,左宗棠只能賭一次。
于是他點頭了,不是信鮑超,而是沒人可用。

小池口對峙:左宗棠臉上無光
1861年,小池口決戰開始。
鮑超手下三千霆軍,對陣的是太平軍陳玉成部,四萬大軍,精銳盡出。
左宗棠不放心,他親自去了鄂南,坐鎮黃岡,他派幕僚跟著鮑超,并限令:“不得擅動主力,斬者勿論。”
但鮑超壓根沒管這些,他知道這是場賭命的仗,官場那一套,戰場用不了。
第二夜,他親自潛入敵營,用火攻燒掉前哨營寨,幾十匹戰馬在火中亂躥,太平軍慌了。

第三天,霆軍出擊,全線沖鋒,太平軍主將被擊傷,前線崩潰,幾萬人后撤。
左宗棠沒料到,他本想讓鮑超拖住敵人,不是真指望能贏。
戰后第二天,朝廷要求各軍上報戰果,左宗棠的奏折里第一次出現:“鮑超之勇,冠絕三軍。”
這話,他寫得手發抖,因為他知道,這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他不想捧鮑超,但不得不捧。

左宗棠“以頌代管”:只要你聽話,怎么夸都行
鮑超打勝仗,軍功一條條上來,但問題也來了,他不受管。
霆軍缺糧,他直接帶兵去長沙逼糧,湖南官府嚇瘋了,上書彈劾:“鮑將軍軍紀不整,擾民甚烈。”

左宗棠怎么做?
他沒罰鮑超,反而在奏折中寫:“鮑將軍體恤將士,不忍部下饑寒,實為忠勇之師。”
這不是左宗棠認了他,而是左宗棠太清楚權力怎么運作。
如果你硬壓鮑超,他立刻反彈,下面將士也跟著走人,他必須找個方式“套住”這匹野馬。
所以他用的策略是:我不派人盯你,我在朝廷面前替你說話,你就別越線。
這就是“以頌代管”。
鮑超頭部重傷時,已經休克,軍醫說“活不了”,左宗棠立刻上表:“鮑將軍身中六創,仍督軍不退,蓋世之忠勇。”
朝廷批示賜金,升官,這一套下來,鮑超服了。
左宗棠不是在表彰他,是在栓他,他不是讓鮑超飛,是讓他飛在自己手里。

霆軍成了“救火隊”,但沒人真的感謝他
湖北戰局失控時,是鮑超救的火。
金口嘩變那年,霆軍欠餉三月,士兵反了,砍了自己軍官,搶了軍械倉,京城震動。
左宗棠沒有出兵,也沒下命令。

他找到曾國藩,說得很直白:“此軍只鮑可撫。”
鮑超臨危受命,進軍三天,只帶兩百親兵,靠嘴收編三千人。
回營后他立刻整軍,五日后,調往嘉應州,擊潰嘩軍主力。
左宗棠第二次上奏,寫道:“亂軍未除前,鮑將軍坐臥營中,夜不解甲。”
但戰后呢?
朝廷并沒有重賞鮑超,也沒有升職,只有一句話:“仍留原職。”

因為他只是左宗棠的將,不是“系統內的人”,不是淮軍,不是京營,不是勛貴,他是個用完即棄的人。
左宗棠心里明白,鮑超這個人,只能用來打仗,不能帶進權力核心。

霆軍 vs 淮軍:血債、壓制、清算
鮑超和李鴻章,注定不可能共存。
兩人第一次交鋒,是在尹隆河。

那年,鮑超率霆軍主力馳援江西,繞道安徽與太平軍交戰,戰斗打得極狠,霆軍陣亡過半,擊潰敵軍。
問題出在之后。霆軍在江北休整,途經淮軍駐地。一個叫吳長慶的將官,把霆軍扣在碼頭,不讓進駐,他說上頭沒批,缺糧,缺地盤。
鮑超火了,當場撂話:“此等行徑,何異敵寇?”
結果不到三日,淮軍后方開始散布消息,說霆軍嘩變過、軍紀差、有亂命之虞。
李鴻章裝作不知情,實際上,是他放的風。

左宗棠急了,他知道這事不能鬧大,他調鮑超回湖南,說是“整軍”,實則避鋒。
從此,霆軍再也沒能在主戰場露臉。
一場硬仗打完,功勞記不住,仇卻記死了。
鮑超那時候脾氣越來越怪,他開始沉默,抽煙抽得狠,曾說過一句話:“殺敵三千,不如一句讒言。”
左宗棠也沒辦法,他清楚這就是系統問題。
淮軍后起,占了北洋重地,有洋槍洋炮,有中央軍餉,霆軍呢?湘軍子弟,靠地方供給,仗打得再狠,最后還是得靠“關系”才能上桌。
他保不了鮑超,他只能讓他退。

中法戰爭:最后一戰,也不讓你贏
1884年,法軍犯臺,朝廷大亂。
左宗棠提議調防,湘軍有一支舊部還在廣西,是鮑超親手帶過的部隊,主將孫開華。
他寫信推薦:“孫為鮑門舊將,性勇,可任重。”

朝廷答應了,但命令里寫得清楚:“僅限臺南以南,不得越境。”
孫開華出征,打得很猛,但死得也很慘,整支隊伍陷入膠林地帶,被伏擊,法軍火力猛,湘軍近戰反沖失敗。
孫開華戰死,霆軍舊部也算徹底沒了。
朝廷沒有立碑,左宗棠寫了一封信,在日記中記:“孫死,鮑部盡,功業無人知,遺恨難言。”

孫開華
那年,鮑超已經死了,他是在軍中染病,咳血而亡,死時五十八歲。
沒有進京,沒有封王,也沒有太廟名號,他一生沒輸過仗,卻沒贏過命。

左宗棠的策略:不是器重,是控制
從頭到尾,左宗棠對鮑超的“器重”,都是一種策略。
不是他信任,而是他太清楚,怎么對待這種人。
鮑超不能罵,要捧;功勞不能搶,但不能全給;軍權要松手,但不能讓他掌握資源;在朝廷面前夸他,在內部設人盯他。

這套玩法,鮑超其實懂,他不說破,也不反抗,他知道,只要能打仗,就還有存在意義。
左宗棠自己也說過一句狠話:“將領無后路,方肯死戰。”
所以他不給鮑超后路,他要他永遠在前線,永遠在火線,永遠只能靠勝利來換口糧。
一旦打不了仗了,就沒用了。
他沒錯,他也沒輸,他只是選了對自己最安全的方式。

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是一群人的命運
晚清不是沒有將才,是將才沒有出路。
湘軍的制度,是“義勇起家”,靠地方士紳撐軍餉,靠團練上位,但只要你升得高了,就有人怕你,只要你打得贏了,就有人壓你。
鮑超這樣的人,不是死在敵人手里,是死在體制夾縫。
左宗棠“以頌代管”,不是為了成全鮑超,是為了穩定湘軍,更為了保護自己。

他在奏折里寫盡鮑超的英勇,但沒有一次,為他爭軍餉、爭官階、爭兵權。
因為他知道,如果真捧殺,鮑超會死得更快。
最終鮑超死了,霆軍散了,湘軍也老了。
淮軍上位,北洋成軍,一代人打下來的江山,變成別人坐的天下。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河南
河南